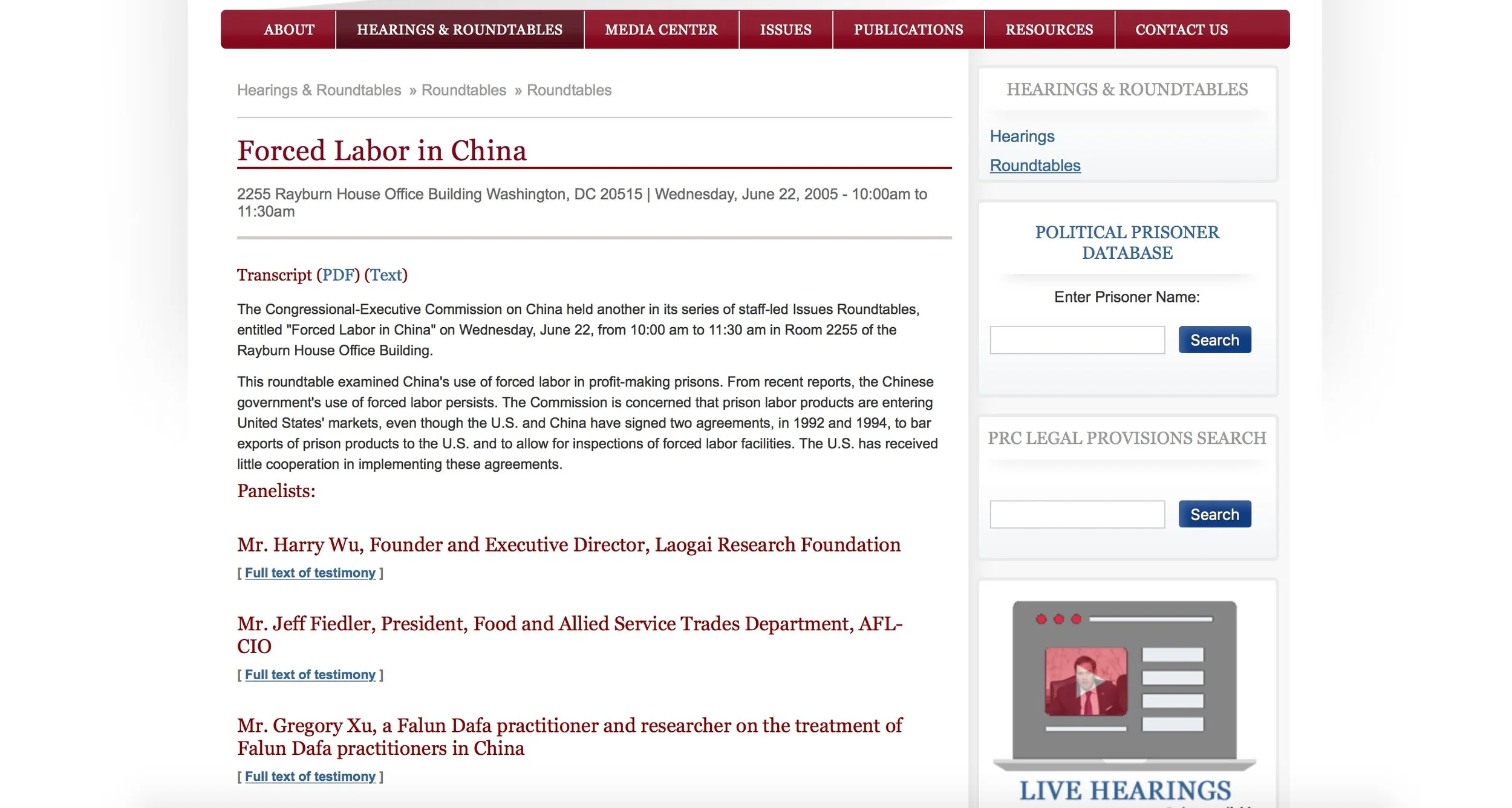楊銀波致《靜水流深》作者的一封信
曾錚:
今天銀波選擇以公開信的方式向你表達我作為一名大陸民間人士的失敗。我對自己每日每夜的拷問到此時此刻所積累的嚴重程度,已經逼迫我必須公開表達這種自責、愧疚、憤怒與無能為力。尤其是當幾乎所有恐懼都被自己戰勝,然而卻在法輪功維權案例上僅僅止於較低層面的呼籲與吶喊時,這種強烈的失敗感超過以往任何一次人生挫折,它源於面對「禁區之禁區」的「恐懼之恐懼」。迫於專政、迫於政治暴力,我被迫喪失了作為「人」的「發現的權力」、「發現的自由」與「發現的能力」。我不能容忍這種恐懼,不能容忍自己有此權力、自由與能力然而最終竟然「被迫喪失」的懦弱、膽怯與嚴重失職。我深刻地反思,作為一名對思想和信仰有著無限尊敬的民間知識份子,截至目前所「發現」的一切,無非都是對先人的重複,了無新見。如慾成其為一個透過層層迷霧便能知其本質與規律的思想家,我楊銀波真是力量遠遠不及,為此我深深恥辱,為此我無地自容。
2003年9月1日,我於《議報》發表強烈抗議當局殘酷迫害法輪功的第一篇文章《面對謊言與虐殺——推介<新世紀紅朝第一謊言>》,當時我並不知道你就是《新世紀紅朝第一謊言》的親筆作者「曹靜」(更未注意到「曾」與「曹」同形,「錚」與「靜」同形)。事隔4月,我終於收到你寫來的第一封信。自2004年1月4日起,至1月19日、1月24日、2月2日,你寄來的信我總是反覆地看、反覆地尋思;而《靜水流深》這本優秀的書,我或許是閱讀遍數和筆錄思考得最多的大陸人之一。為此我將所有筆錄整理歸納,不僅於1月28日列好了書評《論<靜水流深>》一文的總綱,並且已於1月30日列好了對你進行深度採訪的問題提綱。我贊同《靜水流深》這本書裡面所談及的哲學思考,這些思考佔據著道德制高點,比如「大無畏」、「大自在」,比如針對這場迫害的多方面角色的思辯等等。書中所涉迫害人等、迫害方式及其制度安排,對我的良心造成極大震撼,此種震撼基於一次又一次不斷重複和擴張的作為同胞的深度同情、作為公民的嚴重抗議和作為人的本性反抗。我的家人、朋友、同行理解我的這一心情,然而他們卻一次又一次地勸阻我不要寫作和發表《論<靜水流深>》以及採訪你的這一系列行動。這真是一種良心的折磨!
這些年,來自民間對當局的反對力量,只要出於非暴力及理性的立場,我都是不予懼怕的,並視之如手足兄弟,待之如患難之交。然而《面對謊言與虐殺》及其他言論發表之後,我仍然跳不出這個由大面積恐懼所形成的底線——可以撰文呼籲,但不可將法輪功具體的案例細緻地公開化。從事社會調查將近4年的我,遭遇的是最後一個恐懼,也是最大一個恐懼——法輪功。我無法理解自己這種深刻的矛盾:以個性而論,放言大膽乃是我的本色;以交友而論,天下朋友已逾三千;以波擊面而論,更是難以數計;——然而,為甚麼有此本性與優勢,卻自己給自己戴上一副閃閃逼人的手銬?如果僅僅以「迫於專政、迫於政治暴力」就自我解脫,那麼更多更令人理解的理由與藉口不是同樣也可以呼之於口、見之於世嗎?當大陸的鄭貽春、杜導斌、東海一梟、劉曉波、趙達功、余傑等人接連向當局喊出了「抗議」的同時,為甚麼對待法輪功維權案例,我們不能更進一層地公開交流和探討?難道地下、私下的大陸空間就將一直成為一個不可逾越的底線嗎?恐懼啊恐懼,恐懼阻擋了我們;我們啊我們,我們阻擋了自己。
古語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兩千兩百年以來,「天不變」便屬中國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轍的始因。制度無以進步,王朝更迭;道德無以提升,真性虛無;——何以有變?鄭貽春在電話中對我說:「真、善、忍,還略為保守;要真、善、勇。那麼哭泣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忍耐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必須要『勇』。」以我「鬥士型」的性格,考量當今大陸的迫害程度,我同意他的說法;但是考慮到人類社會長久的和諧發展,「忍」比「勇」更能使社會趨於良性化發展。而「真」,毫無疑問這是第一位的。比如將來公民社會的建立,這就需要首先建立「公民」,人格獨立、思想自由這是「五四時期」就提出來的,那麼獨立了、自由了,這個獨立就有真獨立、假獨立和真自由、假自由之分。獨立與自由沒有「真」,仍然等於假獨立、假自由,這比無獨立、無自由更糟,因為自以為獨立自由的人其實並不知道真相,產生了許多偏執狂和空想狂,亦自欺,亦欺人。如果現在這個政權倒台,我擔心大陸並不一定能走向良性發展,為甚麼呢?暴民社會產生的可能性是巨大的。看現時大陸人的普遍心態,崇尚暴力、權力、金錢,假民族主義盛行,以牙還牙,唯利是圖,麻木、虛偽、空虛、浮燥,違背真性(真)與良知(善),反倒顯出許多劣根。
再論「忍」與「勇」。仁、義、禮、智、信、勇,尤其是孟子,前五者繼之,後者「勇」揚之。結果這個「勇」被誤解,今人養習了許多毛澤東的「勇」——霸氣,成了小毛澤東。如果公民社會要建立,小毛澤東們是不能當政的。為甚麼呢?不把自己首先當作「公民」,你如何去引領公民並建立公民社會?對於一個國家來講,最危險的敵人只有一個——政府,執政者彙集,始成為政府,而由小毛澤東們組成的政府只可能面對最危險的敵人——人民。大海,所以能成其為「大」者,蓋因其能居於所有江河之下。這個「大」不是指霸氣的「勇」,反倒是「下」;這個「下」,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忍」。克制、寬容、忍讓、忍耐,然後才能浩大,成其為浩然正氣。當然,這是指道德層面,不是指權術與法制。再進一層地說,即便權術有佳、法制已成,最根本的道德、精神、人格卻很壞,那麼權術只是利器(如當今的所謂「反腐敗」便是如此),而法制也是空談(如當今無法獨立的司法便是如此)。因此,一種信仰能夠使人返樸歸真,從「人」本身的道德要求入手,那麼這種信仰有甚麼可怕的呢?人類社會得以穩定發展,最根本的底座無非有二:第一,生態;第二,道德。至於制度、法律,若無度打擊或瘋狂歪曲這種生態和道德,那麼人類社會要維持穩定與發展便是不可能的。所以,當前我們的第一任務,就是改變這種違背人類社會規律的制度與法律——亦即變「天」,繼而有「道」可變。曾錚,我講的這些,無非都是我作為一個普通公民的看法。
我至今仍無任何宗教信仰,但我知道正統宗教在數千年內將人類社會維持在一定道德水準上的功績。我曾對比中西文化,可知其根本區別在於兩者對未知世界的「發現能力」及其「發現自由」的差異。我是誰?我從哪裏來?我到哪裏去?這三個問題大陸人已鮮為思考;但自即日起,必須重新思考。我反對絕對的唯物主義,是因為一些事情我無法解釋。迄今為止,我所認識的中國文化,其最高水準者依然是古老的《易經》;即便是這樣一本小小的經書,我也仍然無法完全參透。近幾年的調查走訪,使我見識了來自大陸民間的第一流人物,他們被體制所埋葬,然而卻有著驚人的預見和深刻的反思。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直至今日,我知道一些人物的出現是一種必然。我選擇積極入世,然而來自民間的一股思潮卻告訴我:這些人哪一天將怎樣,哪一天又將怎樣。結果不出其所料。這些民間人士迴避世事,耕著自己的良田,讀著自己的老書,早起晚歸,過著自然、平靜、閒適的生活。他們不責備我的努力與爭取,並認為我的出現仍然是一種安排。「還有許多事你必須去做;即便哪天你決定停止這一切,但你還是丟不開這一切的。」他們告訴我,「一直到你將近60歲的時候,你才有空去四川九寨溝那些地方飲酒啊。」也就是說:未來三十多年,我將繼續活躍於世。
我一直樂於進入社會最底層,這些真實的現狀使我比其他更多人感受到更為深切的矛盾;不止法輪功,卻以包括法輪功在內的社會思潮來反觀更多的社會矛盾。我的貧窮與際遇,使我悲憫且豁達;我的貧窮與際遇,使我反抗且更多地關注他人,並在少年時期感悟出「生命本來無意義;一個人為了別人,會讓自己的生命變得有意義」的道理。世界上沒有圓滿,我們應該永遠向更高者學習,向更低者傳授,向優異者敬禮,向醜惡者反抗。那麼面對謊言與虐殺,我們便不能將自己置於漠不關心的旁觀者的地位。我一生所遵循的行動準則,不容許我在這樣重大的時刻無恥地沉默,特別是在同胞的根本權利遭到目無法紀的瘋狂的暴力侵犯的時候。因為此種侵犯違反一切正義原則並踐踏文明國家普遍遵循的法律和協議,若我對此竟然逃避現實或者心灰意冷,則此種羞辱決非我能以言詞表達。我想此信至此,已經說出了我的心聲:無論是你們的災難,還是其他人的災難,若此種災難乃是不適於常理的殘酷迫害,我必然突破限度地仗義相助;若我的限度遲遲無法突破,我將為自己清清楚楚地記上一筆賬,這筆賬遲早都應全數清還。直到我年近黃土之時,我將再次重新細數這一生未還清的筆筆舊賬,把它們一筆一筆地列在我的遺書之上,將此留予大陸同胞與子孫後代,將此留予我即將離開的這個世界。
友:楊銀波
2004年2月3日凌晨 於中國大陸 親筆
附:在《大紀元》,你和章天亮的文章堪稱一絕,令人欽佩。請代我向章兄深表感謝,他的文章深邃、廣博且有力,對我影響很大。今天是中國農曆大年十三,再過六天便是我21歲的生日(農曆正月十九,2004年2月9日),我將在生日這一天為所有深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絕食一日。
本文作者:楊銀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