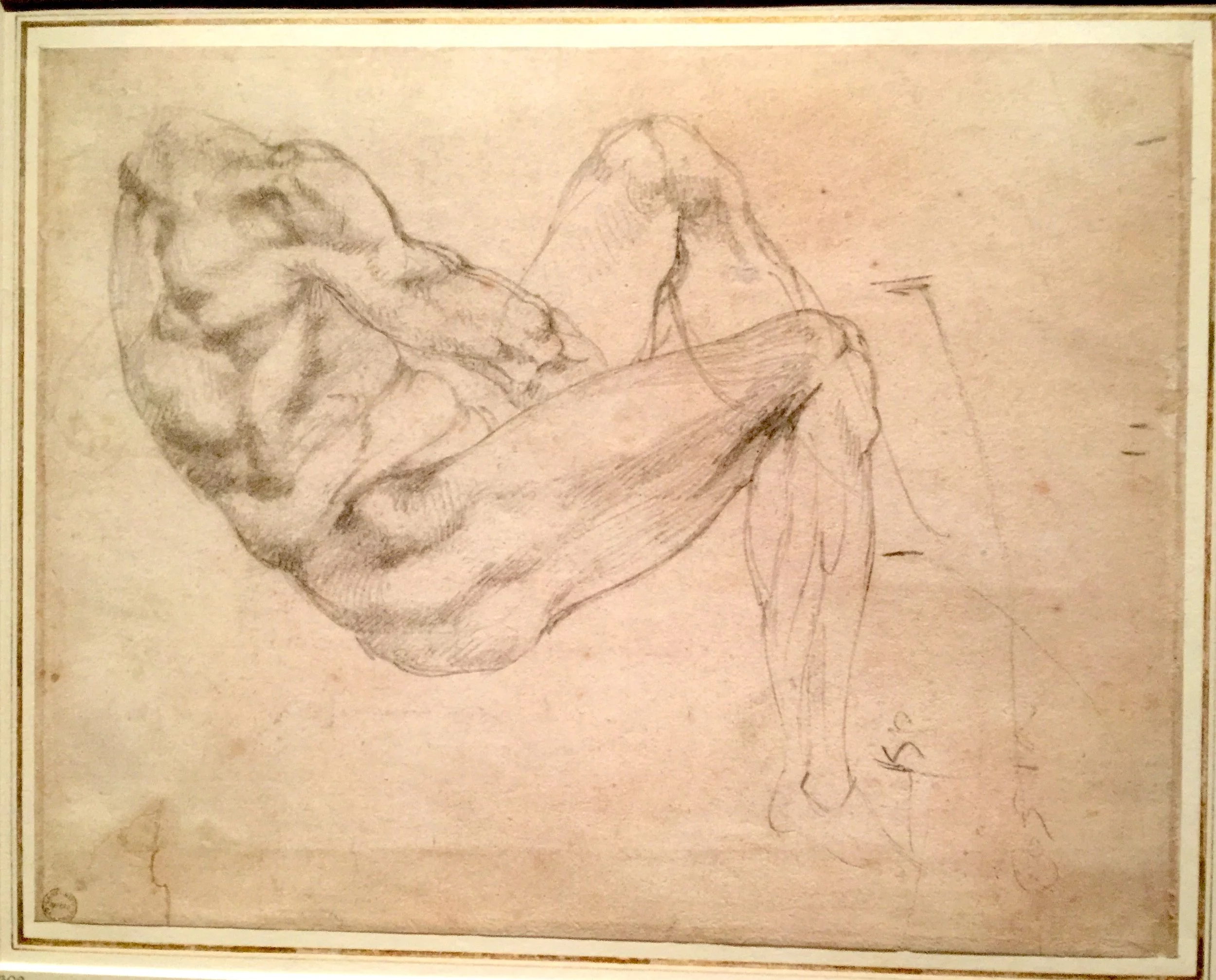政治與文藝創作之間,是創作者實踐尊嚴和自由感的場域
(這份發言呼應主辦單位:「政治與文藝創作之間,是創作者實踐尊嚴和自由感的場域」。)
我是畢業於北京大學的理學碩士研究所,本來與文學無緣,但因命運周折,自2001年到2003年期間,寫下長篇紀實文學《靜水流深》;目前我在澳洲擔任一份中文雜誌的副總編輯。
《靜水流深》這部自傳,今年初首先發行中文繁體字版,並在臺灣登上暢銷書榜,書籍內容由兩條主軸貫穿:一條宏觀的軸線是,中共跨世紀最大規模的人權迫害──即對法輪功的鎮壓;另一條微觀軸線為,個人親身遭遇的真實見證。
我 於1997年修煉法輪功後,醫師宣判藥石罔效的肝疾,奇蹟式地痊癒;但由於中共於1999年7月全面非人道鎮壓法輪功,我因而三度被捕入獄,前後一年餘, 在獄中遭受中國獄史上難得一見的酷刑及種種非人待遇;我對」真善忍」的信仰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殘酷考驗.我所親歷和見證的一切使我產生一種強烈的沖動,要將 這一切記錄下來,獻給現在和未來.它也是一段對我信念持守,生命意義追尋的重大功課。
我秉持法輪功的「真善忍」信念,走過人間煉獄后,我一邊寫作一邊並輾轉逃亡至澳洲。
「寫下來」,只為見證歷史,我本無意涉入政治;就像法輪功學員從不涉入政治。但如同許多文學創作中描述的命運意外,在文學創作與政治參與上,我都遭遇了實際人生的連串意外。
發表《靜水流深》,揭露了中共最大的政治謊言,再度成為中共打壓的對象,它不但自出版之初即成禁書,甚至傳閱《靜水流深》資料的大陸民眾,都可能遭中共拘捕下獄!
政治與文學,都是承載/輸送人類信念的載器(DEVICE),我相當同意二位英國學者在政治上為人民謀福利的共同認識: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以及邊沁的實利主義(Utilitarianism)──:政府的目的,是保障「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政治為管理眾人之事,好的政治人物,真誠為最大多數人民謀求最大福祉;文學為抒懷弘志之事,好的文學創作者,如文化研究者張開焱在<文學與政治關係的理論表述>所說:
如果是一個對人類的生存狀態和命運、對人類生活世界有強烈關懷的作家,就不可能不關注政治,他的創作也不可能不直接或間接涉及政治,中外文學史上眾多著名作家作品都是有強烈政治意圖、政治意向、政治效果的。
就像我們也在孟浪等關懷人權的作家的作品中,永遠可以讀到人道主義的氣息。
法輪功關係到全球上億人的活動,普世的程度,從教授學者到村夫村婦都參與其中。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研究專家何清漣曾說明,她何以討論法輪功這個重大的人權主題註解:「法輪功的爭議見仁見智,但無論什麼人,都無法贊成用如此暴力手段對付一個社會群體。」
浦士納法官曾經註解:「對於公平正義的追求、不能無視於代價。」法輪功已為中共的不良政治體系付出嚴重代價,中共對法輪功鎮壓,也在付出人心向背的代價。
直到今日,中共對法輪功族群施加的迫害,尚未停止,每天都有人死亡,每天都有人在獄中遭受《靜水流深》書中描述的那種慘無人道的酷刑折磨。我在《靜水流深》的書寫,只足以管窺這部史無前例大歷史的一小塊拼圖。
我想,無論是政治家,抑或是文學家,都應該首先遵從超越于政治和文學的天理.希望政治與文學的美好結合,應該不但是追求人性尊嚴與人生而自由的場域,它們更成為實踐宇宙法理的載器,經由真誠善良大忍的政治家/文學創作人,應該謀求最大多數人的、最大的、恆久的幸福。
2004年5月